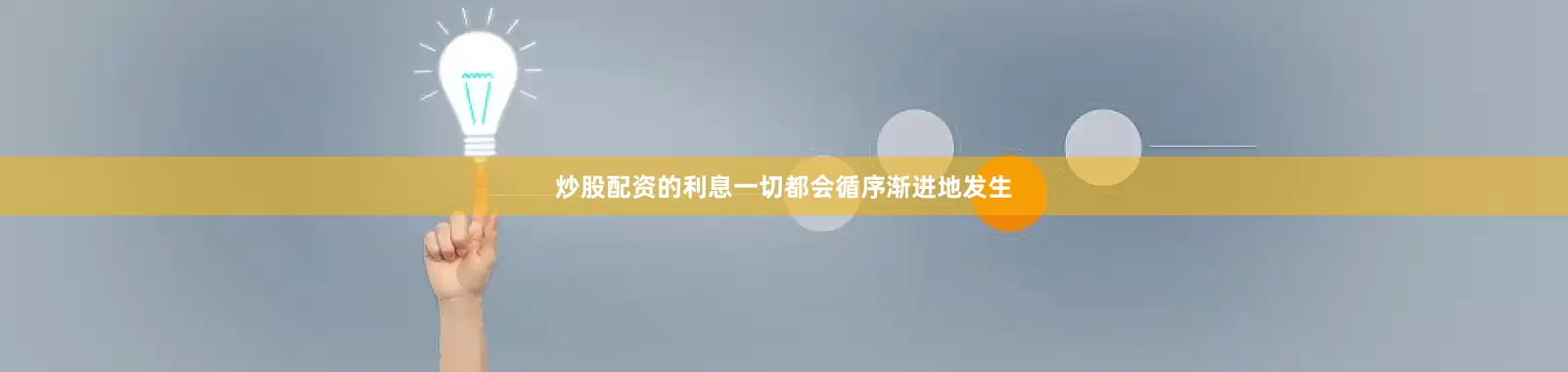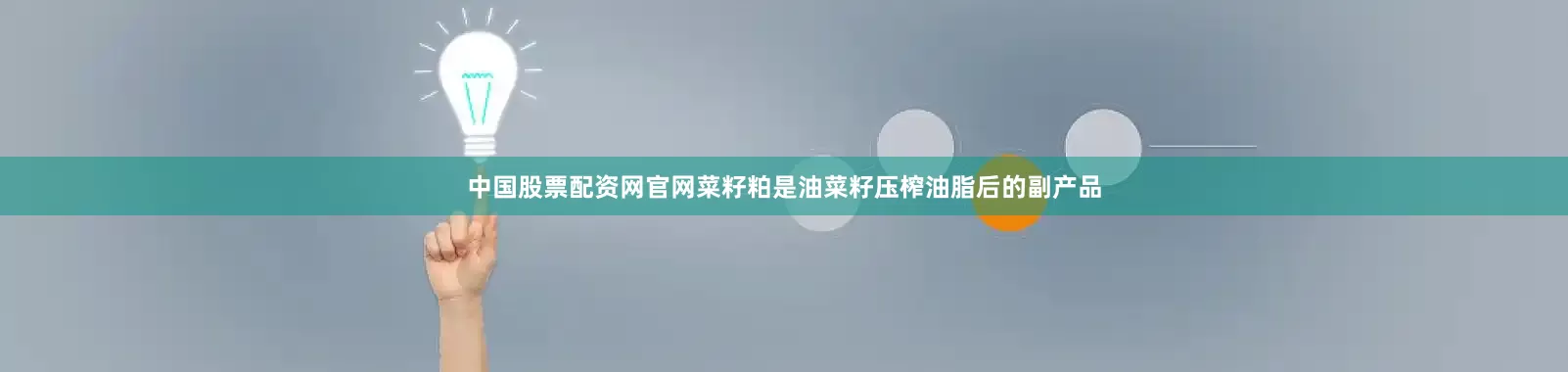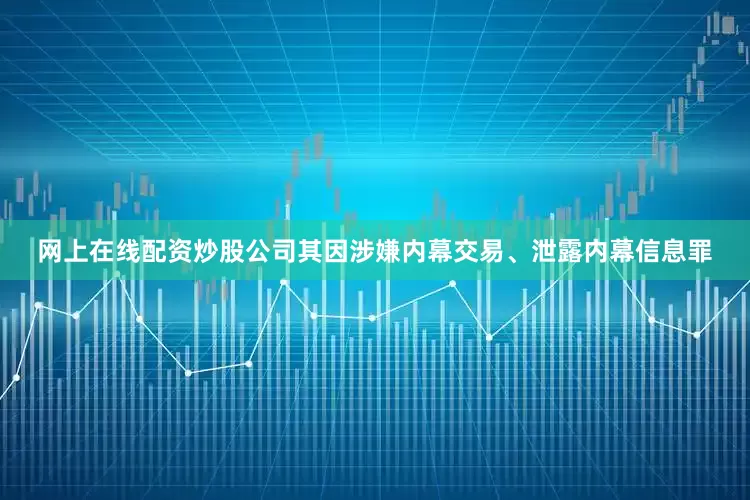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,县城中心的老戏楼前已像被撒了把豆子,密密麻麻挤满了人。穿蓝布褂的老人踮着脚往台口瞅,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棉花糖在人群里钻,卖糖葫芦的小贩扯着嗓子吆喝,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铜锣声盖了过去。“咚 —— 咚 —— 咚 ——” 三声脆响过后,戏楼雕花的木门 “吱呀” 敞开,八个精壮汉子抬着褪色的 “擂台” 木牌走出来,牌上斑驳的红漆里还能辨认出 “技高一筹” 四个金字。这是消失了 30 年的 “庙会打擂”,此刻正踩着元宵节的鼓点,在这片土地上重新苏醒。
说起这庙会打擂的来历,得从光绪年间的县志里找踪迹。当时县城里有三家杂技班子,为了争抢庙会的表演地盘,常在校场摆擂比试。最初只是简单的翻跟头、耍花枪,后来渐渐演变成绝活比拼:张家班的 “走钢丝” 能在悬空的麻绳上叠三层人,李家班的 “吞火” 能同时吞吐三支火把,王家班最绝的是 “顶碗”,演员倒立着用脚接住观众抛来的瓷碗,碗沿相碰时能弹出《茉莉花》的调子。久而久之,这比拼成了庙会的固定节目,每逢正月十五,十里八乡的人都要赶来看这场民间高手的较量,赢家不仅能拿到商户凑的彩头,更能赢得全年在庙会开棚演出的资格。
展开剩余80%官网:http://WWW.WPTCPWM.CN/
1980 年代后期,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外出务工潮的兴起,年轻人大都不愿再学这苦差事,杂技班子陆续解散,打擂的风俗也慢慢被人淡忘。直到去年冬天,县文化馆整理老物件时,发现了一箱尘封的道具:锈迹斑斑的铁圈、磨损的软鞭、还能转动的空竹。馆长是个念旧的人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村里贴了告示,想找些会绝活的老人重办打擂,没想到报名的人从祠堂排到了桥头。
第一个报名的是 72 岁的赵老根,他耍的 “水流星” 曾是当年的一绝。老人颤巍巍从樟木箱里翻出一对铜碗,碗沿包着厚厚的牛皮。“你看这包浆,是我爹传下来的。” 他摩挲着铜碗上的凹痕,眼里泛着光,“当年我爹能把水泼成圆圈,转起来像两轮月亮。” 彩排那天,赵老根喝了半斤家酿的米酒,手腕一抖,两碗清水在空中划出银弧,水珠落地时竟连成串,在青砖地上洇出个整整齐齐的圆。围观的年轻人看得直拍手,老人却皱着眉:“差远了,当年我爹能在碗里养金鱼,转半个时辰鱼都不掉出来。”
官网:http://WWW.CHIJI8.CN/
打擂正式开场那天,戏楼前的石阶被踩得发亮。头一个上台的是个穿黑色紧身衣的姑娘,年纪不过二十出头,却是赵老根的徒孙。她抱着个半人高的瓷缸,缸沿上摞着七只青花碗。随着鼓点渐急,姑娘突然腰身一折,头顶在缸底,双腿腾空劈成直线,七只碗像长在脚背上似的纹丝不动。台下顿时炸开了锅,有人把草帽抛向空中,有人扯着嗓子喊 “再来一个”。姑娘却不慌不忙,借着旋转的惯性,用脚尖轻轻一挑,最顶上的碗稳稳落在肩头,惊得前排观众倒吸一口凉气。
第二个登台的是邻村的王二柱,他表演的 “钻火圈” 带着股野劲。三个铁圈被烧得通红,间隔着摆成 “品” 字形。王二柱赤着膊,古铜色的脊梁上能看到凸起的筋骨,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,猛地冲向火圈。第一个圈他像泥鳅似的滑了过去,第二个圈突然凌空翻了个跟头,第三个圈竟背过身用脚勾住圈沿,整个身子像陀螺般转了三圈才落地。火屑落在他胳膊上,烫出一个个小红点,他却浑然不觉,只是咧着嘴笑。有懂行的老人说,这功夫叫 “凤凰三点头”,当年只有王家班的班主能耍,没想到如今还有人会。
官网:http://WWW.ZHAOZHENGFU.CN/
最让人揪心的是压轴的 “走钢丝”。表演者是个 60 岁的妇人,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,穿一身湖蓝色的绸衣。钢丝被拉在两株老槐树之间,离地足有三丈高,风一吹就悠悠晃动。妇人手里握着根细竹竿,起步时脚腕微微发颤,走到一半突然停住 —— 原来有个看热闹的小孩把皮球扔到了钢丝上。就在众人屏住呼吸的瞬间,妇人突然弯腰,用脚尖勾住皮球,顺势在空中转了个圈,落地时稳稳把球抛回给孩子。台上台下死一般寂静,片刻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,连卖茶水的老汉都忘了收摊,举着铜壶直跺脚。
打擂的输赢由观众说了算。每个人手里都有枚红纸团,觉得谁演得好就把纸团投进对应的木箱。统计结果出来时,夕阳正斜斜照在戏楼上,赵老根的徒孙和王二柱的木箱里各堆着半箱纸团,竟是不分上下。馆长正犯难,穿湖蓝绸衣的妇人突然走上台,把自己的红纸团撕成两半,一半放进姑娘的箱里,一半塞进王二柱的箱中。“都是吃饭的手艺,分什么高低。” 她声音不大,却让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。
官网:http://WWW.XINSHIJIEHUTEL.CN/
暮色渐浓时,戏楼前点起了灯笼,红光映在每个人脸上。赵老根教小姑娘转空竹,竹哨声清亮得像泉水;王二柱给孩子们演示怎么绷直脚背,说这是 “站得稳” 的诀窍;穿湖蓝绸衣的妇人则坐在石阶上,给围拢来的年轻人讲 “走钢丝” 的门道:“心要静,眼要准,脚底下才能有根。” 有人问她为什么愿意把绝活教给外人,她指着戏楼梁上的木雕说:“你看那盘龙,少了一片鳞就不成龙了。这手艺啊,就像龙鳞,得一片一片接着,才能活起来。”
散场的时候,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扛着摄像机,追着老艺人们拍个不停。他是从北京来的纪录片导演,听说了庙会打擂的事,特地赶来取景。“这些技艺再不记录,就真的要消失了。” 他举着镜头,看着赵老根把磨得发亮的铜碗小心翼翼包进蓝布帕子,眼里满是感慨。而在戏楼的角落里,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正学着台上的样子,用跳绳当钢丝,嘴里 “嘿哈” 地喊着,虽然动作笨拙,眼里却闪着亮晶晶的光。
夜风掠过老戏楼的飞檐,带走了喧闹,却留下了些什么。或许是铜碗碰撞的脆响,或许是火圈灼烧的温度,又或许是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。消失了 30 年的庙会打擂,不仅仅是一场表演的重现,更是一代人对匠心的守望。当清晨的阳光再次照戏台,那些年轻的身影会接过老人手中的道具,让 “技高一筹” 的匾额,在新的时光里继续闪光。
发布于:上海市众和策略-众和策略官网-配资短线炒股-南京股票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安全的杠杆炒股平台协同相关部门整合科普资源、开展科普活动
- 下一篇:没有了